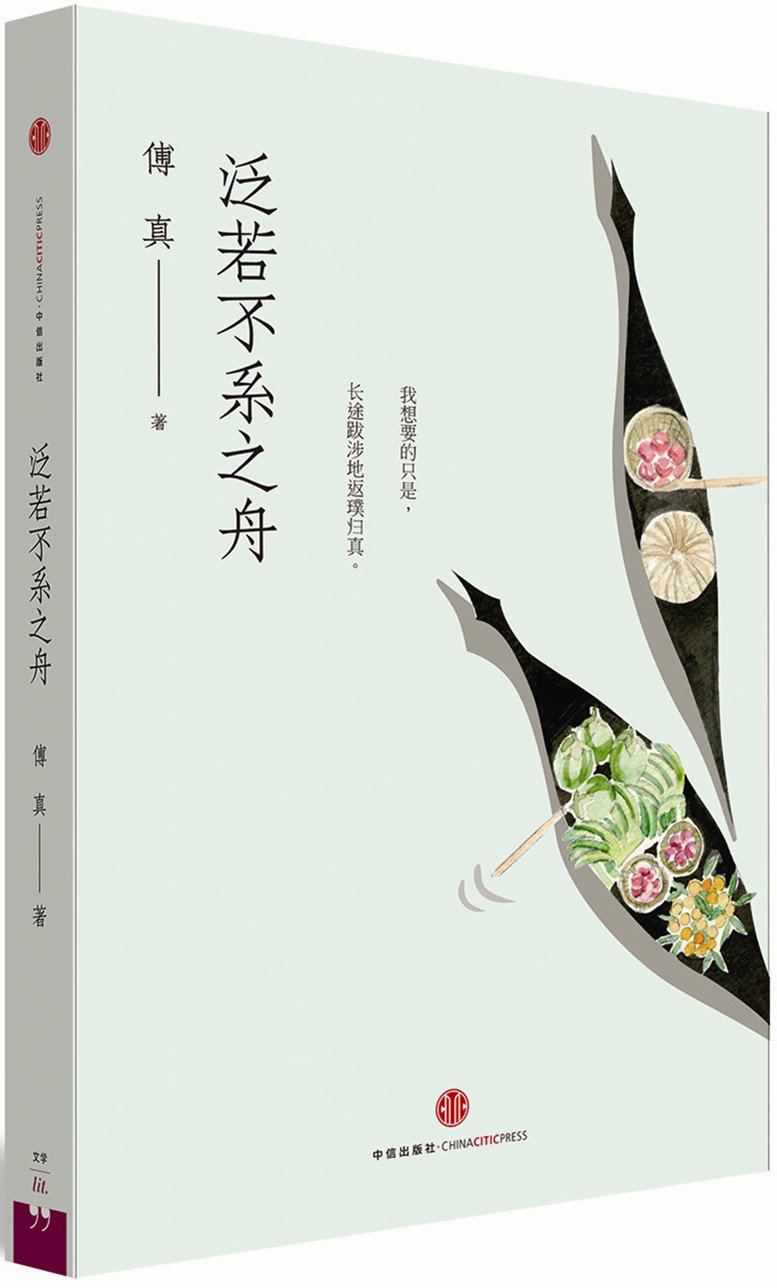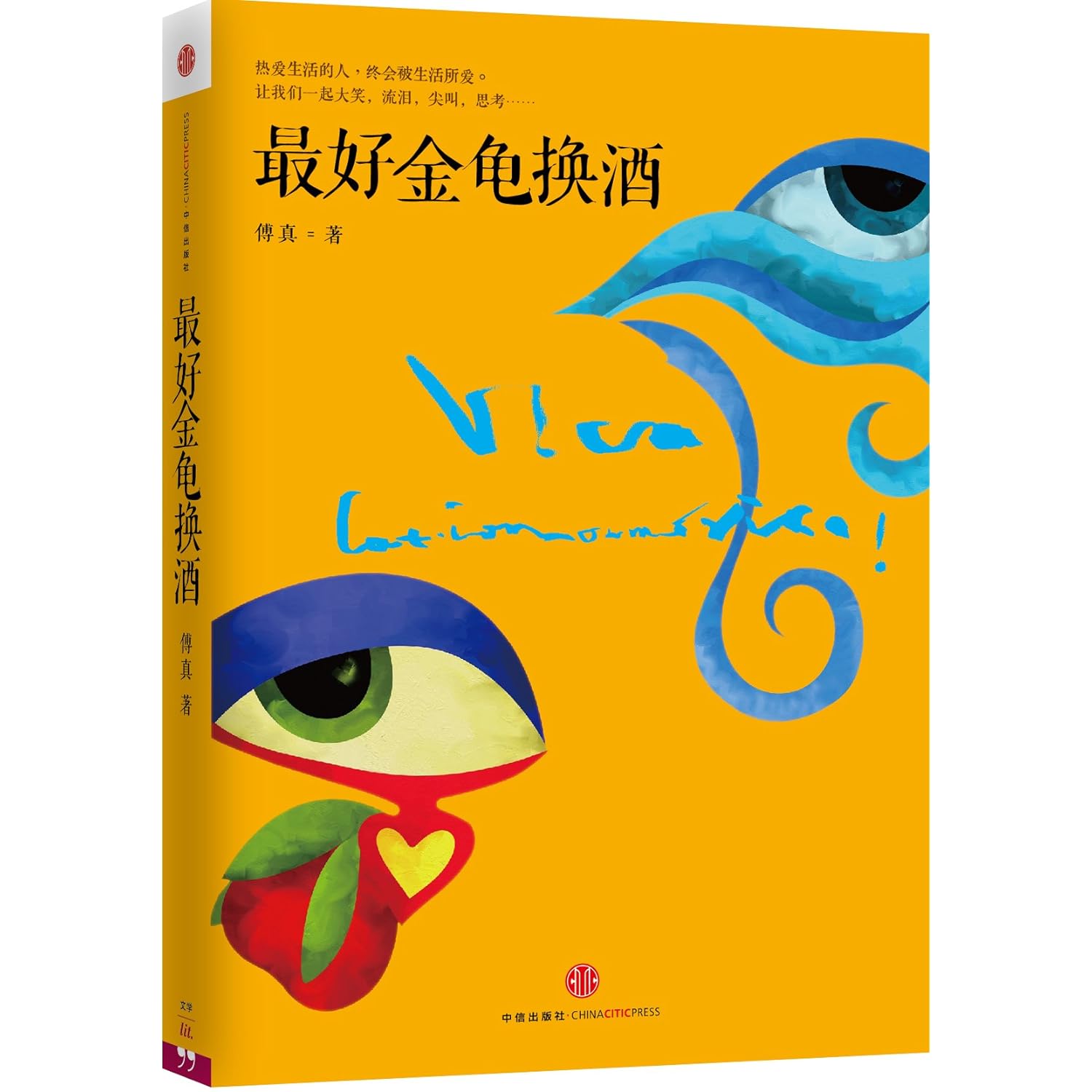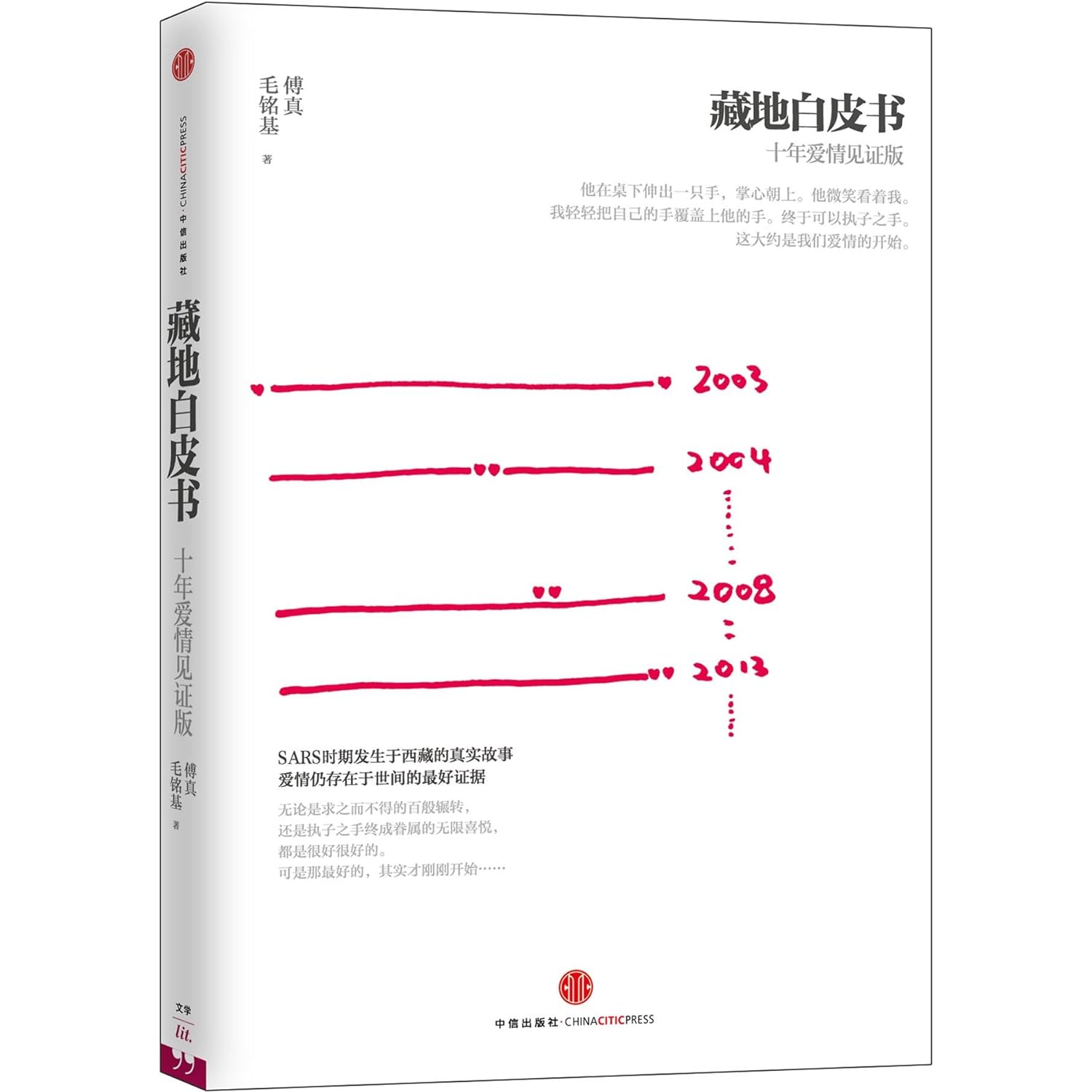Author Archives: 傅真
劫后余生
2022年12月前的北京,空气中有种暴雨将至的压抑和躁动。风咆哮着,仿佛知道它遇见了更厉害的对手。人们淹没在传言、预兆、猜测的洪流之中,一边心火如炽,一边万念俱灰。然后,一夜之间,大船调头转向,暴雨倾盆如注。这边厢还沉浸于见证历史的震惊和恍惚,身边的人们已如风暴中的小麦一批批倒下。退烧药售罄,急诊室爆满,城市因“硬着陆”的冲击而再次陷入荒芜。 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迎来感染高峰的大城市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也是三年来人们第一次公开大胆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病程。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,至少在我的朋友圈中,极少见到恐惧焦虑,更多的是乐观和热切,往往还伴随着自我调侃——从不幸之中找出笑料,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技能。幽默是一种心理防御方式,人们以此来对抗残酷的现实。 毫无意外,很快我们一家也阳了。抗原测出两条杠的那一刻几乎是一个解脱的瞬间:靴子终于落地!因为毛衣的学校在放圣诞假,我们计划趁假期回老家看父母,但又担心带病毒回去传染他们;如今尘埃落定,算算时间,等到阳康后再回去也来得及。如果赶上南昌的爆发期,或许还正好可以照顾他们——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,一两天后爸妈竟也先后测出阳性,是南昌较早感染的一波…… 我们一家三口的病程无甚特别,算是相当标准的轻症。毛衣第二天退烧后就活蹦乱跳了,铭基自我感觉症状轻于流感,我则结结实实地反复发烧了三四天,好在只是头痛背痛,也没有传说中的“宝娟嗓”和“刀片喉”。不得不说,内心还是颇有些挫败的——老娘可是一周上四次keep健身课的人! 但与此同时,我也终于理解了身边朋友们分享经验时那几乎带着喜悦的乐观情绪。那是另一种解脱感,源自免于恐惧的自由——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在自己家里生病了,不用再像仅仅几周前那样,恐惧于被拉走被隔离被歧视,担心牵连邻居,担心孩子的处境,担心家中被消杀,担心宠物没人照顾甚至被“处理”……尽管身体不适,但我毕竟是躺在自己的床上,身处熟悉的环境之中,不用在方舱里排队等待安排床位,频繁使用公共卫生间,在整夜不灭的大灯下入眠……至少在很大程度上,身体和私人物品的掌控权终于回到了自己手中,这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令人安心。 另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娃长大了。在我和铭基发烧卧床的那几天里,毛衣一个人肆无忌惮地从早玩到晚,乐高碎片铺得满天满地,偶尔良心发现,会给老父母做个糖拌西红柿。其实我从未奢求她有多么懂事贴心会端茶倒水嘘寒问暖,不要在不恰当的时间来给我添麻烦——这就是老母亲最大的心愿。托她的福,这回我们终于得以平静地卧床养病,再没有人每隔5分钟便满屋子横冲直撞大喊“妈妈”…… 很难想象孩子究竟要如何理解这一切。从封小区上门磁到轻症可以上班,从每天计算核酸“保质期”到一夜消失的核酸亭,从老师家长反复警告的可怕病毒到每个人都坦然说出“我也阳了”…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,前后不到一个月。当毛衣看到爸妈卧床不起时,她的心里是否曾闪过一丝恐惧?在过去的三年里,她对世界的感知与体验曾怎样被割裂和扭曲? 痊愈后有一次聊起某事,她很自然地接话:“对对……那是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……” 大笑过后,我也忍不住琢磨她所使用的语言。孩子擅长即兴的语言实验,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潜意识的流露,也许在毛衣眼中,经受过病毒洗礼的我们已然成为某种“死而复生”或更难以名状的全新物种。 在许多层面上,我也的确不再是从前的我了。尤其是过去的一年,精神上的压抑和内耗让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枯竭。不想看到那些阴间新闻,但又必须紧紧跟随最新信息,即使它们随时可能会被推翻。产出越来越少,睡得越来越晚,时间白白浪费,感受希望和快乐的能力不断被剥夺,就好像每天都死去了一点点。 是的,现在我们逐渐自由了,可那些沉重的记忆无法也不应被抹除,更何况封控和自由的背后其实是同一双翻云覆雨手、同一套强大而无制约的权力运行逻辑。有时看到网络上的某些分裂和争吵,我也会感到相似的悲哀。在势不两立的观点背后,我看到的是同一种集体的、持续的、未经处理就被吸收和内化的创伤,而那些激烈的表达和无端的戾气其实都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。不在抑郁中爆发,就在抑郁中灭亡。 最近我常想起十年前在泰国禅修时的奇特体验:在十日禅修的后期,打坐时总是莫名其妙地不停流泪,仿佛是在排出过去累积的情绪——为自己曾经遭遇的痛苦,也为一路走来所看到的不幸。那时我才意识到,有些心理创伤会有延迟性。有时我们走了如此之远,远得连悲伤都疲惫不堪。而它所带来的震荡和影响,也许要在几个月或若干年后才会慢慢渗入我们的生命。 出京终于不再是个问题,一路也顺滑得似真亦幻。回家总是令人开心,但这一次还多了几分沉甸甸的“劫后余生”之感——此劫甚至还未尽渡。我们在圣诞节后回到南昌,北京感染高峰已过,南昌则仍在逼近峰值。街面上人烟稀少,要到一周之后才复归往日热闹景象。 好在我爸恢复得很快,妈妈也转阴了,但身体还是虚弱,常需卧床休息。尽管如此,她还是与我们一道出行了好几次,去东林寺拜佛,去鱼尾洲公园散步,去白鹤小镇看候鸟……年少时的我并不懂得欣赏家乡之美,总是向往远方的新奇和大都市的五光十色,直到在“异世界”漂泊经年逆水行舟,才有机会回头重新看清自己的来处。 它甚至比记忆中更好。好与不好的丈量尺度往往随时间而更改,我曾暗暗“嫌弃”它不够时髦光鲜,现在却恰恰为此感到欣慰。这座生态之城并没有被水泥丛林侵蚀,反倒有了更多与自然连接的空间。我鲜少会看着某幢高楼大厦,怀念它曾经是其他东西时的古早时光。 漫步在鱼尾洲公园,我甚至隐约看到了家乡一千多年的样子。“水城共生,城在湖中,湖在城中”是南昌独特的城市形态,而鱼尾洲公园几乎再现了《滕王阁序》中“鹤汀凫渚,穷岛屿之萦”的图景。它的前身是一片备受污染的鱼塘,设计师开辟出有净化功能的湿地,并将鱼塘的泥土和粉煤灰混合在一起,建起一座座漂浮小岛,星星点点,若即若离。湖泊留出了可蓄滞洪水的空间,而为了适应汛期水位上涨,岛屿上的植物也都选择了能在水位涨落中生存的树种,比如落羽杉、池杉和水杉。水上森林被淹没期间,公园就变成了一片沼泽湿地,另有一番野趣。 入冬后的杉树和香樟层林尽染,树影婆娑倒映湖面。落羽杉的叶片如红色羽毛团团簇簇,夕阳又为它们勾出金边。我们沿着亲水步道穿越森林岛屿,君王般的树木和水岸边的大片湿生植物组成一个新生的共和国,缄默的生命如潮汐般滚滚而来,将人类微不足道的存在吞没。 我想起去年春天静默中的北京,许多人都在绝望地寻找一片水、几亩舒展的草地。即使找到了隐秘的好去处,你也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标注它们的位置,因为闻讯赶去的人群会令这些地方立刻遭到封禁。那真是一段荒谬的时光,我们一退再退,退到荒山里、野河边,像打游击一样处处闪避,但有时还没站稳就被驱赶,大喇叭不断重复广播着“不要聚集不要聚集”……我们何以至此?为什么甘愿做西西弗斯?或许是因为太渴望靠近大自然了吧,我想,让自己压抑失控的情绪被那天地不仁的恒常所稀释。 鱼尾洲公园也仍保留了不可为人类探索的秘境。许多岛屿四周并没有步道,那是特地留给鸟儿的栖息之所。作为水乡泽国,江西历来是候鸟天堂。所谓“鹤汀凫渚”、“百鸟佃于泽”、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……正是这片土地人鸟共生的常态。我爸还曾特地考证过那个流行于亚欧非三大洲的“羽衣仙女”传说(美丽的仙女沐浴,男子窃得羽衣后与其结婚生子,仙女取回羽衣后飞返天界),可以认定古代豫章地区(现在的南昌)便是这个故事的故乡。 如果你也喜欢观鸟,我要隆重推荐一下位于南昌高新区鲤鱼洲的白鹤小镇(又名“五星白鹤小区”)。白鹤是江西省的“省鸟”,全世界约有4000只白鹤,98%以上都在鄱阳湖越冬。小时候我爸会特地带我坐很长时间的车去鄱阳湖看白鹤,没想到如今南昌周边便有环鄱阳湖区域白鹤数量最多、观赏距离最近的观鸟点。这里原本是五星垦殖场的一片藕田,自从大批白鹤来此啄食莲藕,农民不堪经济损失,打算改种水稻;幸好有爱鸟人士发起了“留住白鹤”众筹活动,筹集到足够资金租下藕田,整修道路,建立水位调控系统,建起了首个民间白鹤保护小区。 我们在一个起风的阴天来到保护区。天地萧肃,渺无人烟,走在观鹤长廊上,颇有“风声鹤唳”之感——我从未意识到鹤类是如此“嘈杂”的生物!据说鹤的气管长约1米多,是人类气管长度的五六倍,宛如一柄弯曲的长号,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,其声可传至数千米。所谓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野”,它们简直像是在开交响乐party。 透过围挡的缝隙窥看,水田里密密匝匝一片白色,鹤舞蹁跹,风姿绰约,展翅飞翔时会露出黑色的翅尖。间中点缀着黄色的身影,那是白鹤的幼鸟,每年秋天随家族南迁至鄱阳湖越冬,次年春天飞回西伯利亚时已变成白色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中的黄鹤,很可能就是古人看到的白鹤幼鸟。来年都变成白鹤了,当然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啦——只是不知道崔颢本人是否了解个中缘由…… 白鹤的迁徙路线原有东、中、西三条。在鄱阳湖越冬的白鹤属于东部迁徙路线,中部路线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到达印度,西部路线则是沿着里海西海岸到达伊朗。然而在过去20年里,由于战乱和盗猎,中、西两条迁徙路线已几近丧失。东部路线硕果仅存,鄱阳湖已成白鹤的最后一片家园。 年复一年南渡北归,仿佛永恒的轮回,又像是时间的守护者。白鹤说着自己的语言,专注于它们流动的宿命,并不关心人类的叙事。“万物皆流动,无物常住”——2500年前的赫拉克利特从对自然的观察中得出结论,几乎带着几分禅意。世间万物在流动中生生不息,在交互中生发变异,彼此依存,共生共处。在无法流动的日子终告结束之际,面对流水、浮云和漫天鹤影,我也觉得自己略微更靠近了命运。 但命运会嘲弄我们,在你大谈“流动”时发出冷笑声。2022年的最后一天,我们正驾车前往海昏侯博物馆,坐在前座的老爸突然对着手机惊叫出声: “小卢哥……走了?!” 那是我的小舅舅,因新冠导致呼吸衰竭,永远留在了2022年的冬天。 和许多“候鸟”式老人一样,舅舅舅妈也习惯于随季节迁徙的生活。他们平日住在成都,每年冬天则飞去温暖的西双版纳旅居,没想到这次竟倒在了越冬之地。感染后以为是感冒受凉,没想到已经入肺,送到当地医院抢救了几日,最终也无力回天。特殊时期一切从简,遗体立刻火化。去西双版纳时全须全尾,回程却只余一坛骨灰。我的小舅舅再也无法“流动”了。 车子飞驰向前。我把手机贴到耳边,听着微信群里舅妈泣不成声的语音。等清明节回南昌,她哭着说,把骨灰撒入赣江,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心愿了……妈妈,毛衣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,你很难过吧……我没有说话,我爸也没有说话,语言在此刻似乎全然无用。我难过吗?冷风从车窗缝隙里渗进来,有些情绪似乎被冻硬了,需要时间慢慢将它化开。 我们继续前行,开进博物馆的停车场。我伸手去开车门,却发现自己要被一股强大的倦怠和荒谬感压倒了。时间本身不大对劲,哀悼和玩乐之间一些必要的步骤丢失了。我们真的要去博物馆吗?不然又还能怎样呢? 讲解员在给我们介绍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奇珍异宝,我失魂落魄地跟在后面,在历史长河的角落打捞个人记忆的吉光片羽。上次见到小舅舅是2020年秋天的北京,妈妈这边的亲戚们从天南海北齐聚一堂,为我的大姨庆祝九十大寿。我们还一起去了故宫看展览,出来后等了很久才叫到网约车,几位老人只得在路边枯坐。记忆最后的画面定格在车子驶离的那一刻,他摇下车窗,微笑着朝我们挥手——那个刹那的悲怆意味要到此时才全然落地。北京的大姨和长沙的大舅舅在一年后相继离世,没想到又一年过去,小舅舅也猝然长逝。 我努力回想他的样子。妈妈的大家族多是“自来卷”,小舅舅又格外高鼻深目,常被戏称为“外国人”。他温柔细心,永远笑眯眯,总是热情邀请大家去成都玩……这是从刘贺墓中出土的金饼,讲解员提高音量,一共100枚,就铺在垫着遗骸的琉璃席下……我贴近展柜欣赏那金光灿烂的珍宝,却蓦然从玻璃反光中看到自己的脸——茫然、渺小、无知无觉的愚蠢和自私。你沉浸于劫后余生的团圆之乐,直到本以为遥远的哭声响彻耳边。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一切呢?一边是歌舞升平重迎人间烟火,一边是脆弱的生命像野草一样被收割。一边对失而复得的生活心存感激,一边又要随时准备接受亲人的离去。(回到北京没几天,我的阿姨——我妈最亲近的姐姐——也因感染新冠抢救无效而去世。)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——我好像直到此刻才读出它残忍的深意。如果我曾为放开而欣喜,是否意味着如今要承受良心的谴责?如果活着才是第一要义,我们是否甘愿牺牲一切使生命变得有价值的东西?我们是否可以一直坚壁清野,直到经济民生都难以为继?电车难题终究无解,事实上也根本轮不到普通人来做选择,我们却为何如此习惯于自我反省,以至于社会责任和统治关系都可以轻松地隐身而去? 可是,痛苦和愧疚也都是真实的。人心比道理更千疮百孔,我们注定只能在死亡的阴影下活着。 或许这也是应对现实的唯一方式吧:one reality here, one reality there. … Continue reading